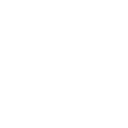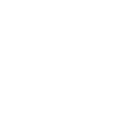半岛BOB新闻报道与环境问题我们对环境问题的理解和行为反应,不仅依赖环境科学,也依赖媒介再现。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传播频率和传播形式对我们的态度、感知和行为都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早期的理论假设媒介效果是从传者(信源)到受者直接传递信息的结果。这种早期理论将受众看作极易受控制的人,并把人群看作“一块同质的潮湿海绵,被统一浸泡在来自媒介的信息里”。这种研究路径很少得到支持,而且因为它在解释环境媒体的影响方面没有提供特别有用的东西,于是其他的论述出现了。这些论述超越了对个人的某种特定影响的研究,而进入到塑造议题感知、建构社会叙事等范围更为广泛的媒介影响上。
接下来bob半岛·体育,我将回顾关于新闻报道对公众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的三个主要理论。这三个理论分别是:(1)议程设置;(2)叙事框架;(3)培养分析。虽然这些研究路径几乎没有提供任何直接的、有因果关系的证据,但它们认为媒介的影响是累积的,是帮助建构我们对环境的兴趣和理解的社会影响的一部分。
也许媒介效果理论中对环境新闻最有影响的理论是议程设置。科恩是第一个提出议程设置概念的人。他用这个概念区分个人意见(人们所相信的)和公众对一个问题的显著性或重要性的感知。他认为:“新闻报道也许大多数时候在告诉人们‘怎么想’方面做得并不成功,但是在告诉它的读者‘想什么’方面却异常成功”。在对电视的研究中,艾扬格和金德这样定义议程设置:“这些在国家新闻中受到明显关注的问题成为受众眼中国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bob半岛·体育。”
议程设置假说对很多环境传播研究都形成了影响。这些研究“明确证实,媒体在公众所关心的环境问题和公众对环境问题的知觉上发挥着强大的议程设置作用”。但有时候研究结果也是相互冲突的。艾扬格和金德在对电视晚间新闻的研究中,发现了议程设置效果的有力证据,认为观众在观看了越来越多的对环境污染的报道后,把环境问题放到了更重要的层面上。艾亚尔、维因特和迪乔治以及阿德、索拉达发现议程设置在不引人注目的议题,以及读者和受众没法接触的议题上效果特别明显。最明显的效果就是媒介增强了受众对来源于环境的风险或者危机的感知。
另一方面,艾扬格和金德发现没有明显的证据支持电视新闻报道在其受众对环境议题的重要性的感知方面产生了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报道一个有毒废弃物地点和对一个生病的孩子的母亲令人心碎的访谈,并将两者联系起来,或者报道中只有一个记者在解释化工生产基地和灾难性疾病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这两种方式在吸引受众关注相关问题方面并没有太大差异。
但是,环境传播学者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反对否定议程设置的效果。阿德指出,除了新闻报道,真实世界的状况也会影响人们对问题重要性的感知。安德森还指出了其他的影响要素,比如朋友和家人都可能影响公众对环境问题重要性的感知,而议程设置研究应该把这些要素也考虑在内。
为了完善议程设置理论半岛BOB,阿德调查了现实世界条件、以及媒体议程的影响,她研究了《纽约时报》从1970年到1990年的环境新闻报道。由于该研究被认为是一项标志性研究,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进一步加以讨论:
阿德提出了两个问题:(1)受众对环境问题的关心,究竟更多地是受媒体报道驱动还是受现实世界的条件驱动?(2)受众的态度影响了媒介的报道数量,而不是媒介对议程的设置?阿德使用了盖洛普公司在这个阶段的调查问卷bob半岛·体育,确认受众周期性地将某些问题界定为“国家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为了控制和真实世界状况对媒体报道的影响,阿德研究了盖洛普调查之前和之后三个月《纽约时报》中关于污染的报道的长度和显要程度,同时还从独立来源处搜集了同时期真实世界中垃圾处理、空气质量和水的质量等方面的数据。
阿德的研究确认了强效果的存在,尽管将现实世界的条件和之前的都考虑在内了。也就是说,尽管在研究期间,客观测量表明整体污染水平在下降,但《纽约时报》增加了对污染的报道,报道长度的增加和显著度的增强,都与随后读者对该问题的关心程度的增强相关。但是,反过来的结论并不成立,也就是说媒体并不是在反映公众。阿德总结道:“研究说明,媒体对污染的大量报道影响了受众对该问题的关心程度半岛BOB半岛BOB。”
虽然议程设置假说可以解释一个议题对公众的重要性,但它并没法表明人们是如何思考这个问题的。因此,我们还必须去了解其他理论,以关注媒体在构建环境问题的意义和受众的理解方面扮演的角色。
如前所述,新闻媒介不仅传播关于环境问题的事实bob半岛·体育bob半岛·体育,而且传播理解和把握这些事实的框架或方向。所以,媒介效果理论开始关注意识的形成或者是框架,这些帮助我们解释了新闻报道在协调我们的经验和我们与环境的关系方面扮演的角色。这些理论并不认为媒介报道催生了,相反半岛BOBBOB半岛,它们声称,“媒体话语是个人构建意义的过程的一部分”。
叙事研究模式很重视媒介框架的作用,认为它将新闻报道中的不同元素连成了一个整体。叙事框架指的是媒介通过故事将现象的片段组织起来的方式,它可以帮助受众加强理解,也可以激发受众的潜力,通过组织故事来影响我们与被再现的现象之间的关系。这种框架的观点建立在传播学学者罗伯特·恩特曼对框架的定义上:“框架就是选择特定现实的方面,让它更为显著……通过这种方式为已经描述过的问题提供问题定义,阐释事件原因,提供道德评价,示意解决方案。”换句话说,媒介框架可以通过提供叙事结构——问题是什么bob半岛·体育、谁应该负责、解决措施是什么等来组织一个新闻报道中的“事实”。
詹姆斯·沙纳罕和凯瑟琳·麦克马斯是这种理论的主要支持者,他们发现环境新闻报道“几乎从来就不是对‘事实’的简单传递”;相反,“记者运用叙事结构构建了有趣的环境新闻报道。……记者和媒体工作人员必须吸引受众半岛BOB,他们必须用打包的叙事呈现他们的信息”。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思莱荷特维格早期做的一个研究——关于美国公共广播公司针对“地球优先!”的者所做的报道的叙事框架研究。
1990年5月,《地球优先!杂志》宣布了“红杉夏天”的开始,环保分子们涌入了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红杉森林,“以非暴力方式封锁了伐木道路,而且爬上大树以‘保护树木不被砍伐’”。“地球优先!”的组织者强调,反对非暴力的人将会被禁止参加“红杉夏天”的活动。“地球优先!”还试图和伐木工展开对话,建议他们在新成长的森林而不是在旧的区域里进行可持续的砍伐,这样他们双方就有了共同的利益。
然而,那个夏天,伐木工人、“地球优先!”的环保分子以及农村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升级。在1990年7月20日,公共广播公司的《麦克尼尔莱勒新闻时间》播出了一则关于这项的报道——《聚焦伐木僵局》。思莱荷特维格研究的正是这则报道,以及报道中针对伐木工人、“地球优先!”的者、社区居民以及暴力的叙事结构。
在对《聚焦伐木僵局》的分析中,思莱荷特维格明确地揭示出电视报道主题框架中关键的视觉和语言表达,包括原始森林的画面,说“小城镇经济”依赖“木材”,对用斧头或短柄小斧把树钉敲打入树的特写,以及公共广播公司记者的画外音:“‘地球优先!’有公民不服从的记录,它损坏私人林地,破坏伐木机器……还鼓励大家使用树钉以使大树不被砍伐”。在这个9分40秒的新闻报道的结尾, 故事通过“主人公”和“反对派”的紧张冲突明确了他们的身份bob半岛·体育,提示了真实的暴力发生的可能。
在节目中,主人公的形象通过一些关键的身份和价值观术语被描绘:报道介绍了“工人”“伐木者”和“普通人”,他们的生活依赖“木材采集”和“小镇经济”,这是他们的“工作”“生计”和他们的“生活方式”。相反,报道把“地球优先!”的者描述为“灾难的”“激进的” “错误的人”“”以及“暴力的人”bob半岛·体育,为了拯救“高大且美丽的树”,他们参与“对抗”“钉树”“破坏”以及“公民不服从”运动。思莱荷特维格认为,在《聚焦伐木僵局》这则报道里,这些名词和其他动词以及视觉表达一起清晰地建构了这样一个叙事:这是“普通人”与一个 “暴力的恐怖主义组织,一个想要使用破坏活动……树钉等去拯救红杉林的组织”的对抗。
在媒介影响方面,培养模式与叙事理论相关。沙纳罕这样描述培养分析:“它是一个讲故事的理论,它假设重复曝光一系列信息可以导致受众形成与这些信息的内涵一致的共识”。就像它的名字所反映的一样,培养并不对受众产生即刻或者是特定的效果;相反BOB半岛,它是一个渐渐影响或累积效果的过程。这个模式与媒介研究者乔治·格伯纳的研究相关。格伯纳认为:
培养是文化所致。这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尽管文化是人类生活和学习的基本媒介······严格地说,培养意味着某种特别的、一贯的且有说服力的符号流在复杂的社会化和文化化过程中带来的某种特定的、独立的(不是孤立的)贡献BOB半岛。
格伯纳的研究只关注观看电视暴力的长期影响——对“世界综合征”的世界观的培养。这种世界观将社会看作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人们互相伤害。
同样,运用培养分析理论的环境传播学者对媒体对环境态度和行为产生的长期影响感兴趣。也许令人惊讶的是,这项研究表明重度观看者常常对环境问题的关心程度更低。在一项大学生电视观看行为的研究中,沙纳罕和麦克马斯发现,对电视的重度观看可能会阻碍亲环境态度的形成:“如果说媒体对环境的关注会带来更多的社会—环境担忧,那么这项研究的结论与之并不一致。电视重度观看者对环境的关心更少,这说明了相反的一点:电视中的信息在发展对环境的关心上设置了一个‘刹车闸’,尤其是对电视重度观看者而言”。
有趣的是,沙纳罕和麦克马斯还发现,对比较积极的学生,在观看了大量电视节目后,对环境问题的关心的减弱程度大于其他人。这个发现与我们之前所谈论的议程设置效果相矛盾,即对一个主题的报道越频繁,它的显著度会增加。这该怎么解释呢?培养理论的研究者将其解释为主流化模式,即差异在趋向某一个文化标准的过程中缩小。沙纳罕和麦克马斯认为,就环境媒体而言半岛BOB,电视一贯的信息流可能让人们更接近主流文化,而(被电视节目所呈现的)主流一直是“更接近最低层级的环境关心程度”。
电视重度观看者对环境的关心意识减弱还有第二个解释,即沙纳罕等人所谓的反向培养。也就是说,由于媒介中一贯缺乏环境图像,或者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其他的非环境故事,就会培养出一种反环境态度。由此,通过忽视或者被动地描述自然环境,电视将环境问题的重要性边缘化。培养理论学者也将这个现象称为“符号灭绝”——媒体通过对主题间接地或者消极地不予强调来抹杀一个主题的重要性。
与针对经常观看电视这一行为的主流效果研究的一般结论不同,最近关于电视观众对环境风险的感知的研究有些令人意外。该研究旨在通过更仔细地区分电视频道的多样性来支持培养分析理论,它研究的电视频道包括有线电视新闻网、探索频道、福克斯新闻以及喜剧频道。结果,研究发现了接触更多样的电视节目与对环境风险的关心程度的相关性,这种电视节目多样性的影响超过了观看电视的次数(频率)和(观看者的)个体差异的影响。
我们很难明确找出新闻媒介对公众的观念和行为产生的具体影响,尤其是短期内的影响。媒介的影响可以是复杂的、非线性的。然而,议程设置、叙事框架、对观众观点的长期培养等理论还是认为媒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如汉森所观察到的,“媒介可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化情境,通过这个文化情境bob半岛·体育,不同的公众获得了理解环境问题的词汇和框架,也得到了更多针对特定环境问题的主张的词汇和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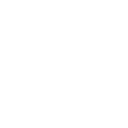

13988888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