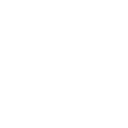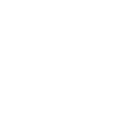半岛BOB理解数字新闻业:新闻生态系统理论了解一下本期为你推送的是Sage于2016年出版的《数字新闻学手册》中的一篇文章。关注的主题是当下数字新闻实践中形成的“新闻生态系统”。作者在简要概述了新闻传播研究中“生态”一词的两种研究路径后,介绍了两者在数字新闻研究中的应用,以及它们如何拓宽了数字新闻研究的想象力。
在本期推送中,我们为你介绍了这篇论文中的核心观点。推送内容仅为对论文的介绍,不能作为学术引证使用。如需引用相关内容,请阅读论文全文。在公众号后台回复“生态”,可以获取本研究文献。
新闻学者翟立泽曾认为,当今新闻业的许多重要事件并不发生在新闻编辑室本身,由此,她提出了“走出”新闻编辑室的研究思路。本文将进一步讨论数字时代“走出”新闻编辑室的概念。我首先回顾了学者们了解新闻编辑室内外的不同方式,随后提出我们可以采取的另一条道路,也就是新闻研究的生态系统方法。“生态系统”一词在媒体研究中存在“媒介环境”和“根茎”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每一种都可以拓展数字新闻研究。

在2004年出版的《认真对待新闻业:新闻与学术》中,芭比·翟立泽认为编辑室民族志存在许多盲点,无法把握传统新闻组织边界以外的各种新闻实践。这和科特尔的一项提议有着相似之处:在新的、相互渗透的数字传播环境中,新闻生产不再以组织为中心,而是越来越分散在多个地点、不同平台上,可以由世界上不同地方的、甚至是流动中的记者进行生产。
本质上看,所有新闻研究的目标都是回答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为什么新闻是这样产生的?新闻对世界、对读者或对两者有什么影响?最后,从规范的角度来看,这些新闻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如何有助于维护一个健康的?批评家们认为,基于新闻编辑室的方法对新闻生产模式的外部因素、对消费行为关注太少,也未能将生产、消费和新闻编辑室本身至于历史语境中。
为了应对这种批评,研究者采纳了三种研究路径了解新闻编辑室的外部因素。第一是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者以此关注新闻编辑部外部的强大科技力量;第二种是80年代到90年代的新闻消费研究;第三是历史视角探索新闻编辑室与外部的关系。

以上的三条路径:/经济、文化和历史—都标志着一种走出编辑室的方策略,他们都放弃了民族志,或是将民族志作为一种补充的方式半岛BOB。然而,是否有一些可以“颠覆”编辑室,但同时保持民族志的视野、现象和意义导向的方法呢?我认为,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将新闻生产外部的结构性因素进行简单分类。我们也可以研究整个新闻生态系统。我把它定义为一个特定的地理社区内,或者围绕一个特定问题的参与新闻生产和消费的个人、组织和技术整体。
大多数的民族志研究主要着眼于大型、传统的中央的新闻机构的编辑室,然而不同的媒体和机构产生着不同形式的新闻和不同的故事框架,在不同的人口群体和公民阶层中传播;这些故事、框架、技术和记者穿越数字和物理空间,本身也影响着其他故事。新闻生态系统并非今日才有,一直以来都有各种另类的新闻生产群体、但在一个新闻生产的边界变的模糊、新闻在数字空间的传播和反弹的速度极快的时代,它有着特别的共鸣。

媒介生态系统的第一条学术路径可以在传播学的子领域中找到,我将其称之为媒体研究的“生态”方法,它的实践者称之为“媒体环境学”,这是一个广为人知的研究学派/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半岛BOB,是“生态学”隐喻在多个跨学科领域中大规模扩散的一部分。媒介环境学认为人类处于媒体“生态系统”或“媒介环境”的中心,而这种生态系统极大的影响了人类的感知、认知和行为。
尽管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者来自不同领域、想法并不相同,但他们都对媒体形式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多伦多学派将传播生态系统隐喻中“自然导向”延伸到了不同媒体类型的进化、增长、衰退和平衡的程度上。例如,媒体生态系统中的媒体形式通常被理解为不同物种—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平衡,如果生态系统健康,它们就会协调一致。偶尔也会灭绝或者进化成更适合当前环境的东西。

2005年,马修·富勒出版了《媒体生态学》,这本书不仅瞄准了由波兹曼创造的媒体生态学传统,还将媒体考古学、设计、计算机科学等领域之间的各种线索、行动者网络理论结合在一起构建了另一种观点。富勒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深度非人性化的媒体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并非位于传播环境的中心,而是一系列不断变化的象征性和物质性媒体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在这些重叠的网络中,最终的结果并非控制论的平衡(如媒介环境学传统),而是动态的、根茎式的扩张。
总结而言,旧的媒介生态学方法以自然世界为隐喻,将不同形式的媒体视为个体“物种”,认为这些物种之间的主要互动模式是控制论式的平衡,并将人类主体置于自然生态系统的中心,我们可以称之为“环境方法”。新的媒介生态学方法认为自然世界和技术世界之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不同的媒体形式具有自然和历史的偶然性。空间运动是由于权力的扩散和形式,而非为了达到平衡。人并非任何媒体系统的中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根茎方法。
但是这些对生态学的不同理解对新闻研究意味着什么?它如何帮助我们走出新闻编辑室?接下来我想谈谈这些生态隐喻在新闻研究中的应用。

正如本章导言部分所述,应对数字时代新闻业不断变化的技术、文化和经济结构的,超越传统新闻编辑室民族志,研究更大的“新闻生态系统”中的网络、机构、社会群体和组织可能是我们的第一步。我想进一步推进这一观点。生态系统的环境和根茎观点都可以用来研究数字新闻,但它们最终代表了新闻研究的不同进路。
在奈特基金会、芝加哥社区信托基金会旗下展开的一系列媒体生态研究中,他们对特定地理或者主题领域内,媒体和新闻机构进行了分类,这些机构包括但不限于传统媒体机构。他们研究这些机构产生的信息,以及这些产出对创造“整体健康”公民的贡献。例如芝加哥信托社区基金对芝加哥本地新闻生态系统的一系列研究,主要关注芝加哥媒体生态系统的新进入者。报告一方面建立了芝加哥新闻工作者的分类数据库,另一半通过社区和非营利组织的焦点小组,确定了哪种新闻更适合芝加哥居民。这与波兹曼对信息环境的态度密切吻合。
明确借鉴生态研究第二条路径的新闻研究要少的多,很多都属于新兴的“大数据和传播”研究的一部分。这类研究的典型例子是吴等人的论文,他们研究了“谁在推特上对谁说了什么”。他们区分了Twitter的精英用户和普通用户,以及社交网站上的个人和组织,使用了大量的数字工具绘制信息在网络上的传播情况,从而重新审视了两级传播的问题。这项针对Twitter的研究并未把分析的重点放在区分不同种类的媒体上(媒介环境的路径),而是关注信息如何在数字和物理空间中扩散,从而激活包括人类和非人类在内的特定节点。
在第二种路径中,我们还可以多采用细致的、人种学的定性研究来研究根茎的实地发生过程。我的一项研究就发现,新闻不是轻松地、动态地在数字和物理空间中移动,而是被各种行动者、活动家和感兴趣的新闻团体积极推动的半岛BOB。简言之,新闻在数字空间中的传播不是一个无缝的传播过程,而是充满了不同参与者在各种物质和准物质结构上推拉内容的过程。
如果这两种路径有些难以区分的话,我们还可以以博客和新闻为例来理解。在环境路径中,博客和新闻是两种不同形式的新闻写作,它们互相影响,最终以不同方式为公民健康做出贡献。在根茎路径下,博客和新闻被合并成一个更大的半物质网络。
这两种方法对于研究“新闻生态系统”的概念都是有用的方法,选择哪一种路径取决于我们具体要研究的问题。当然,前一种路径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已经颇为普遍。第二种路径,在大数据分析以外,我们还可以多展开民族志的新闻生态系统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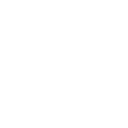

13988888888